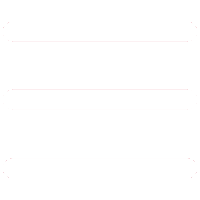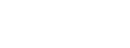張道一先生2009年8月出版了一本自選文集《張道一文集》,這應是道一先生出版的第8本個人文集。與其他7本文集不同的是這本選集具有總結(jié)性和代表性,一方面是所選論文一部分來自這7本文集,更主要的是作者從自己50余年學術(shù)探討的路徑出發(fā),對自己學術(shù)研究涉及的領(lǐng)域做了大致的歸類,并按照這些分類選擇有代表性的文章,以展示其概貌。我以為,作為先生的自選集,所選文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不僅范圍廣泛,更重要的是其理論的深刻性和學術(shù)建樹。
道一先生在其自選集中將所選論文分為:1、藝術(shù)與藝術(shù)學(包括藝術(shù)美學);2、造型藝術(shù)與美術(shù)學(包括書法和建筑藝術(shù));3、工藝美術(shù)與設(shè)計藝術(shù)(包括圖案學和紋樣);4、民間藝術(shù)與民藝學(包括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研究和民俗藝術(shù)研究)四個方面。這四個方面,基本上涵蓋了道一先生50余年學術(shù)研究的基本范圍,也揭示了其學術(shù)研究的基本路向,他從民間藝術(shù)的學習與研究出發(fā),或者說以民間美術(shù)、民間工藝為學習和研究的基點、原點,進而進入工藝美術(shù)、設(shè)計藝術(shù)研究、美術(shù)學研究,最后在藝術(shù)學的高點對上述藝術(shù)進行整體性的理論思考與探討。這是道一先生基本的學術(shù)路向,是其學理建構(gòu)的一個根本所在,也是其基本學術(shù)思想的本質(zhì)內(nèi)涵之一。
在數(shù)十年的研究中,其路向如此,但也不是線性的,而是多元交叉式的,如近些年對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研究,似乎又回到最初的民間藝術(shù)研究,但概念和思考的深度已大大不同了。當然,就先生學術(shù)研究的整體而言,這些近300萬字的研究論文僅是其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他出版的專題性研究著作如《麒麟送子考索》、《漢畫故事》、《美哉漢字》、《畫像石鑒賞》、《中國木版畫通鑒》、《考工記注釋》等50余種,不僅字數(shù)遠遠超過了論文的數(shù)量,其深度亦有不同的呈現(xiàn)。因此,若對先生的學術(shù)思想作一整體評述,可以說十分困難,不僅面廣量大,而且需要認真的解讀與思考才能初窺其一角。
本文就《張道一選集》的相關(guān)主題和論文,分四個部分對道一先生的學術(shù)思想談一點自己讀書體會,并就此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民間藝術(shù)與民藝學
民間藝術(shù)是藝術(shù)的母體、本源,道一先生稱其為“本元藝術(shù)”。他出身在山東的一個農(nóng)民家庭,在鄉(xiāng)下讀高小,住在農(nóng)民家里,“所接觸到的都是傳統(tǒng)文化”,生活在民間藝術(shù)的養(yǎng)育之中,因而對民間藝術(shù)充滿著真摯的感情和愛。在進入專業(yè)學習以后,更是從理論上認識到了“民藝”是一切藝術(shù)之本的道理。他認為:“千百年來,中國的民間藝術(shù)自生自滅,猶如山花爛漫,成為廣大勞動者生活的一部分。對于創(chuàng)作來講,民間藝術(shù)既是藝術(shù)之源,又是藝術(shù)之流。”他在《張道一論民藝》的扉頁寫了一段散文詩:“民間藝術(shù)是從勞動者心中長出的花,花開花落,自生自發(fā),猶如群星燦爛,仿若百川江流。質(zhì)樸率真,心曲自來唱;喜怒哀樂,由情而生發(fā)。它沒有宮廷藝術(shù)的雍容華貴,也沒有文人趣味的自命清高,更無宗教宣傳的說教。外表的粗、俗、野、土,卻尤顯雨露清新、茁壯美好。為什么要登“大雅之堂”呢?它自有廣闊的天地,最大的空間。在“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之間,并無截然的界限,不是說“俗到家時便是雅”嗎?啊!民藝!你是民族文化的一塊重要基石,是心靈之表、文化之根,藝術(shù)家從這里取法借鑒,理論家由此探討人文。欣賞民藝,會使人想起生長的故土,——那鄉(xiāng)音、鄉(xiāng)情之美;研究民藝,會使人深刻地理的藝術(shù),——藝術(shù)與生活之緣。”
道一先生的民間美術(shù)研究就是建立在這種真摯的情感和本真的認識之上的。他無數(shù)次考察鄉(xiāng)村、城鎮(zhèn),拜訪農(nóng)民、手工藝人,進行民間藝術(shù)的調(diào)研考察,僅發(fā)表的相關(guān)文章就有150多篇。這是他建構(gòu)民藝學的基點和原點,作為一個理論工作者,他對民藝不僅充滿感情,更充滿理性。早在1988年,他就發(fā)表了《中國民藝學發(fā)想》一文,呼吁建立中國民藝學。他認為,嚴格意義上的民藝學,“是一門社會科學,它帶有邊緣學科的性質(zhì)。在它的周圍,必然與社會學、民俗學、藝術(shù)學、美學和歷史學、考古學、心理學等相聯(lián)系相滲透。”在對“民藝”、“工藝”、“美術(shù)”、“藝術(shù)”、“民間美術(shù)”、“民間工藝”等諸多概念作了闡釋以后,提出民藝學研究的六個方面,包括:民藝學的研究對象、民藝學的研究宗旨、民間藝術(shù)的分類、民間藝術(shù)的成就(實存)、民藝學的比較研究以及民藝學的研究方法。他指出,一般的民藝學探討民藝的原理和規(guī)律,主要解決一些有關(guān)民藝的基本問題,而中國民藝便是在這原理和規(guī)律的指導下探討中國的民藝,找出中國的民藝的特點,并解決中國民藝研究中的一些實際問題,他倡導從建立和擴充研究隊伍、從全面調(diào)查研究入手,進而更進行系統(tǒng)的分頭研究。
2000年的新世紀之初,為民族的振興計,他又寫了一篇更為深入論述中國民藝學建構(gòu)的論文:《建立“民藝學”的必要性》。其基點是將民藝學作為藝術(shù)學的一個分支進行全面構(gòu)建,不僅在具體內(nèi)涵上又有了很大的拓展和深入,在建構(gòu)方面亦更具理論的系統(tǒng)性。在民藝學的研究對象方面,指出其包括了大眾生活與藝術(shù)有關(guān)的方方面面,如日常實用的民藝、裝飾陳設(shè)的民藝、傳統(tǒng)節(jié)令的民藝、人生儀禮的民藝、宗教信仰的民藝、健身娛樂的民藝、生產(chǎn)勞動的民藝等等。在民藝學的研究宗旨方面,他提出,應在民族文化整體建構(gòu)的總前提下,具體探討民間藝術(shù)的規(guī)律,包括它的發(fā)生與發(fā)展、性質(zhì)與定位、功能與作用、流布與承傳、種類與風格、成就與特點以及與藝術(shù)家創(chuàng)作的關(guān)系等等,在民藝學與其他學科的關(guān)系陳述中,他指出,民間美術(shù)與一般美術(shù)的繪畫、雕塑、工藝等并非橫向的并列關(guān)系,而是縱向的基礎(chǔ)關(guān)系,這是包括許多研究者在內(nèi)的大多數(shù)人都沒有真正厘清的一個關(guān)鍵問題。
對民藝的研究,作為藝術(shù)學研究的一個分支,并非僅僅研究其藝術(shù)形式或相關(guān)內(nèi)容,還需要從文化和生活的層面上去探討,在《中國民間文化論》一文中,道一先生從文化學的角度去看民藝,發(fā)見民藝的一切皆是文化或謂是具有文化的本質(zhì)內(nèi)涵,正因為是民間的一種生活文化,因此是生生不息的,他認為民藝的未來,因其文化的本質(zhì),而具有利用、轉(zhuǎn)化和再創(chuàng)造的價值和功能。在《民藝研究的若干關(guān)系》中,他對民間藝術(shù)的文化內(nèi)涵作了更深刻的揭示,讀書識字的書本文化的有無不能作為衡量民藝是否是文化的尺子,民藝和民藝的作者可能不識字,但你不能說他們是“沒文化”。
在民藝學的建構(gòu)方面,道一先生不僅撰寫了上述總體性論述的文章,更高的是具體考證、調(diào)研一類的“小文章”,其“小”并非是文章文字之短小,而是指其作為個案研究之細之實。如《年畫論列》、《小鳩的歌》、《女紅之路》、《張果老倒騎驢》、《藍花的變奏》、《金橋、銀橋、奈何橋》及寫紙扎藝術(shù)的《魂歸何處》、寫剪紙農(nóng)婦《剪花娘子庫淑蘭》、泥塑藝人俞湘漣的《泥土情深》等等,真正是洋洋大觀,150余篇論民藝及民藝學的文章,在中國藝術(shù)學研究界,尚無第二位吧?
二、工藝美術(shù)與設(shè)計藝術(shù)學研究
民藝是其他學術(shù)的基礎(chǔ),工藝美術(shù)也不例外。道一先生曾說:“在我的研究中,之所以將民藝和工藝美術(shù)同時思考,是因為二者有很多東西在性質(zhì)上是一致的,只是制作者的身份不同。”就道一先生的學術(shù)研究而言,對民藝的研究和思考實際上開始于從事工藝美術(shù)史論研究之時。先生1953年成為陳之佛先生的入室弟子,陳之佛先生是著名的工筆畫家,也是中國現(xiàn)代藝術(shù)史上第一代從事工藝美術(shù)、圖案乃至藝術(shù)設(shè)計教育和研究的學者,道一先生之所以投入陳之佛先生門下,不是為了學習工筆畫,而是研修圖案和工藝美術(shù)史論。在當時乃至80、90年代,在藝術(shù)界、專業(yè)院校多數(shù)人都認為繪畫高于工藝,工藝乃工匠之物,同樣登不了大雅之堂。而道一先生也許是生性使然,亦或是命中注定地選擇了圖案和工藝美術(shù)史論研究,并立志為工藝美術(shù)正名、維護工藝美術(shù)的尊嚴,他為此寫下了一系列論著,從《本元文化論》、《造物藝術(shù)論》、《跛者不踴》到《美術(shù)傳統(tǒng)的四種渠道》,不僅為工藝美術(shù)應有地位大聲疾呼,更是為工藝美術(shù)理論體系的建立而憚精竭力。可以說,道一先生是中國當代工藝美術(shù)學的奠基者,他從理論上深入論證了工藝美術(shù)和設(shè)計藝術(shù)之間的前后關(guān)系,論證了兩者不僅體現(xiàn)了人的基本創(chuàng)造,顯現(xiàn)出人的本質(zhì)力量,推動著生活的進步,亦成為人類文明標尺的基本理論,提出在諸多藝術(shù)中,工藝美術(shù)因其文化的特質(zhì)“有條件率先進入人文科學”領(lǐng)域。這些獨特而深刻的理論和認識是在社會上普遍輕視工藝以繪畫為高的氛圍中思考和加以闡釋的,不僅需要理論上的洞察力,更需要為真理而前行的那種骨力和精神。
《為生活造福的藝術(shù)》一文,寫于1985年9月,收錄在先生的第二本文集《造物的藝術(shù)論》(福建美術(shù)出版社,1989年版)中。全文分“原始的造物活動”、“用與美的統(tǒng)一”、“與科技同步發(fā)展”、“意匠籌度之美”、“迂回之路”和“為生活造物”六個部分,探討的主要問題是工藝美術(shù)的基本性質(zhì)、藝術(shù)特點和社會功能。論文從“原始的造物活動”的歷史回顧中揭示了工藝美術(shù)作為藝術(shù)起源的最早存在:“人們從最初的造物活動中,逐漸找到了合理的形,也逐漸認識了這形體之美。如果沒有舊石器時代幾十萬年的經(jīng)驗積累,便不可能有新石器時代陶器的產(chǎn)生,更不可能有精美的彩陶制作”,亦即沒有其他藝術(shù)的誕生。“用與美的統(tǒng)一”,則是對工藝美術(shù)本質(zhì)的揭示:“工藝美術(shù)的基本性質(zhì)是用與美的統(tǒng)一。……因為要求在生活中實際應用,必須強調(diào)實用性,充分發(fā)揮其功能;又因為人們時時處處要接觸它,產(chǎn)生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必須強調(diào)審美性,使人賞心悅目,在精神上得到一種鼓舞,在這里,物質(zhì)和精神的雙重作用被創(chuàng)造性地統(tǒng)一在一起了。”道一先生指出,唯有把握住實用與審美的辯證統(tǒng)一,才能從本質(zhì)上理解工藝美術(shù)的內(nèi)涵,不論探討工藝美術(shù)的社會作用,還是研究它的價值,都不能離開實用與審美這兩個方面。在“意匠籌度之美”中,他指出:“設(shè)計一詞,一般與英語的design相對譯,同時也譯作圖案和意匠。”這是對中國近現(xiàn)代設(shè)計歷史有了深切的考察之后所作的陳述。論文通過對工藝美術(shù)的陳設(shè)品作為工藝美術(shù)的代名詞的現(xiàn)象予以闡釋,并在“為生活造福”的部分,揭示出工藝美術(shù)的價值不僅在于美化生活,“更重要的是充實生活、豐富生活、創(chuàng)造生活”。
在20世紀90年代,道一先生對工藝美術(shù)理論的系統(tǒng)思考最具代表性的論述是《造物的藝術(shù)論》。全文共8個部分:誰是造物主、為什么要造物、實用與審美、本元文化、科技與藝術(shù)、物質(zhì)文明與精神文明、民族化與現(xiàn)代化、走向未來。本論文可以說是上一論文的進一步系統(tǒng)化和深化,它集中地反映了道一先生的工藝觀、設(shè)計觀和對工藝美術(shù)學的系統(tǒng)思考。如在“實用與審美”部分,道一先生認為工藝美術(shù)的重要特點表現(xiàn)在資生、安適、美目、怡神四方面,前兩點屬實用性,后兩點屬審美性,實用是第一性的,審美是第二性的。在“本元文化”部分,他從文化研究的角度,對工藝文化作為本元文化進行了深入的論述:“人類創(chuàng)造的文化,首先是兼有物質(zhì)和精神而不可分離的“本元文化”,這就是工藝美術(shù)。”20世紀80、90年代、民族化與現(xiàn)代化的爭論此起彼伏,在“民族化與現(xiàn)代化”一節(jié)中,道一先生聯(lián)系工藝美術(shù)的歷史和現(xiàn)狀對此進行了闡述,他指出:“工藝美術(shù)就其主流來說,是一種在日常生活中直接供人享用的藝術(shù),為了生活的方便和舒適,尤其要強調(diào)群眾的習慣性和普及性。在這里,民族化便是一個核心。……民族化可以理解成民族風格和民族特色,亦即大家常說的中國氣派。”民族化與現(xiàn)代化不是一對矛盾:“所謂現(xiàn)代化,就其品物來說,便是結(jié)合現(xiàn)代科學技術(shù)、適應現(xiàn)代生活方式和現(xiàn)代的審美情趣。……將民族化和現(xiàn)代化割裂開來、對立起來的觀點,顯然帶有表面性,也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
道一先生對工藝美術(shù)歷史和理論的研究,如果從1953年隨陳之佛先生學習圖案及工藝美術(shù)理論、1956年隨龐熏琹先生學習工藝美術(shù)理論和參與編輯《裝飾》雜志的前身《工藝美術(shù)通訊》算起,至今已逾50年。可以說,道一先生既承陳之佛、龐熏琹這些中國近現(xiàn)代工藝美術(shù)第一代學者之學統(tǒng),又開工藝美術(shù)研究之新風,作為現(xiàn)代工藝美術(shù)研究的第二代學者的旗手,他的理論探索與創(chuàng)建深深地影響著后隨的學子們。
1989年,我在中央工藝美術(shù)學院讀博士研究生期間,因開工藝美術(shù)概論課而完成了30余萬字的《工藝美術(shù)概論》的寫作。1990年,道一先生來北京參加會議,我請他審讀書稿,先生并欣然為之作序,在序中他寫到:
??
至于工藝美術(shù)的性質(zhì)和特點,就其主流來說,我確認了以下幾點:
(一)合著生活的脈搏,滲透于衣食住行用;
(二)與科學技術(shù)結(jié)合,相為表里同步發(fā)展;
(三)實用與審美統(tǒng)一,在造物中顯現(xiàn)理想;
(四)物質(zhì)與精神一元,促進兩個文明建設(shè)。
這是一個提綱式的粗略的輪廓。具體情況要復雜得多,須要作具體分析并作出合理的判斷。
這是先生再一次對工藝美術(shù)的理論建構(gòu)作的整體性闡述。不難看到,拙著《工藝美術(shù)概論》其基本理論和思路大多得益于在道一先生身邊學習和工作的四年,我作為先生的入室弟子,朝夕相處,先生的為學為人一直成為我們的楷模。道一先生作為中國當代工藝美術(shù)學研究的領(lǐng)路人,早在改革開放初的1982年便接受了編寫《工藝美術(shù)概論》的任務,由于先生執(zhí)著于更深一步、更完善的思考,同時他亦將這種思考的延展和學理的建樹通過培養(yǎng)學生而交到了后學身上,“為有一群愿為工藝美術(shù)的理論建設(shè)獻身的青年而快慰。”我想,我作為其中的一員正是在道一先生的學術(shù)指引下而前行的。
三、造型藝術(shù)與美術(shù)學研究
道一先生雖長期浸淫于民藝、圖案、工藝美術(shù)研究,但他治學的特點是既在其中,又在其上,往往在一個更廣闊的區(qū)域、更高的視點看問題。他的民藝學和工藝美術(shù)學研究不是孤立的、片面的研究,而是置于美術(shù)學或謂之“大美術(shù)”的大視野下的研究。
在《我說“大美術(shù)”》一文中他寫道:“我們應該建立起大美術(shù)的思想和觀念,防止那種狹隘的小美術(shù)的思想損害。”所謂“小美術(shù)”的思想,是那中以繪畫為主的思想。“我們應該提倡‘大美術(shù)’,平等地對待美術(shù)的各個門類”。實際上,這對于學術(shù)研究而言,同樣涉及到一個視野和方法論的問題。對于這一問題,先生在《跛者不踴——談美術(shù)史論研究中的傾向》一文中有更透徹的表述:“我這里所講的‘美術(shù)’,是大概念的范疇,即包括通常所指的五大塊:繪畫、雕刻、建筑、工藝和書法;所謂‘理論’,應是完整的‘美術(shù)學’。在學科的建設(shè)上,我是主張?zhí)岢觥佬g(shù)學’來系統(tǒng)構(gòu)成的”。因此,他指出在美術(shù)史的研究中至少有四種傾向需要加以注意:一是以漢族為中心,忽視了其他五十五個民族;二是以中原為中心,忽視了周圍的邊遠地區(qū);三是以文人為中心,忽視了民間美術(shù);四是以繪畫為中心,忽視了其他美術(shù),從這些論述中,我們不難看出道一先生在美術(shù)學建構(gòu)上的整體觀和系統(tǒng)觀。
除了大的學科性的系統(tǒng)建構(gòu)外,道一先生亦十分關(guān)注個案研究和對個別現(xiàn)象的觀察與解剖,并用以闡釋大的道理。在《論藝術(shù)的反撥精神》一文中,他曾以《中國美術(shù)報》發(fā)表的畫家谷文達的兩篇短文作為消極的反撥之典型,并對其進行了從文字學到藝術(shù)學的個案分析,指出中國當代美術(shù)的創(chuàng)作和學術(shù)研究存在的一些問題,認為只具有反撥精神,不等于有反撥的能力;他倡導積極性的反撥,而反對消極意義上的反撥,提倡理論研究中深層的理性思考。
在美術(shù)史論的個案研究方面,如對漢代畫像的研究,也幾乎延續(xù)了先生數(shù)十年時間,而成果集中中呈現(xiàn)幾乎是在近幾年。他做個案研究,也總能站在理論的高度上思考問題。在《深沉雄大的藝術(shù)——漢代石刻畫像概說》一文中,他指出,畫像石刻是漢代的藝術(shù),“人們在當時的物質(zhì)條件下,選取了石頭和磚頭作為藝術(shù)的載體,注入以生命,使堅硬冰冷的東西帶著溫暖,產(chǎn)生情感,創(chuàng)造了藝術(shù)的輝煌”。“因此,就藝術(shù)方面來看,不論是對其藝術(shù)成就進行分析還是對其歷史的研究,特別是有關(guān)藝術(shù)的原理,它是怎樣形成的,又是怎樣發(fā)展的,探討一些規(guī)律性的問題,顯得十分必要。”這篇研究漢畫像的個案論文,第一部分的主題便是“藝術(shù)的進化論”,通過今人對畫像石藝術(shù)的所謂定性歸類諸如“擬繪畫”、“擬雕刻”、“準繪畫”、“準雕刻”的分析,指出其“實際上顛倒了事物發(fā)展的關(guān)系;“如果以生物的‘進化論’作比較,藝術(shù)成長與發(fā)展,也有自身的過程。總是由簡而繁,由單一到多樣。”其它的論題也大多從漢畫的個性分析起而論述藝術(shù)的共性,如“關(guān)系性的律動”、“再現(xiàn)和表現(xiàn)”、“平面造型的章法”、“夸飾和隱喻”等等。這種從個別到一般、從現(xiàn)象到本質(zhì)、從小到大、從點到面、從實踐到理論的思考,反映了一個學者理論研究的素質(zhì)和應有的能力,這方面道一先生為我們作出了榜樣。
作為一個藝術(shù)院校的專業(yè)教師,道一先生從事高等專業(yè)藝術(shù)教育已經(jīng)超過50 年。其間他寫過多篇關(guān)于美術(shù)教育的論文,如《美術(shù)教育的社會使命》、《塑造人的大業(yè)》、《新世紀的美術(shù)教育》等等,這些論文作為其美術(shù)學思想的一部分同樣是我們分析其美術(shù)學理論的關(guān)鍵,限于篇幅,在此只好提而不論了。
四、藝術(shù)與藝術(shù)學研究
道一先生說民藝學是藝術(shù)學的一把鑰匙。有了民藝學研究這把鑰匙,20世紀80年代后期,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由點到線到面,道一先生將研究的重點轉(zhuǎn)向了藝術(shù)學研究,探討藝術(shù)的基本原理以及相關(guān)的美學問題。可以說,這是道一先生晚年用力最多的一個領(lǐng)域。經(jīng)過多年的探索,1995年4月他發(fā)表了《應該建立“藝術(shù)學”》的論文,對在當代中國建立藝術(shù)學的必要性和藝術(shù)學的學科內(nèi)涵、理論體系等一系列問題作了闡釋,這是一篇關(guān)于中國藝術(shù)學的具有綱領(lǐng)性價值的文獻。
道一先生指出,藝術(shù)學是“研究藝術(shù)實踐、藝術(shù)現(xiàn)象和藝術(shù)規(guī)律的專門學問,它是帶有理論性和學術(shù)性的、成為有系統(tǒng)知識的人文學科”。也就是說,應把藝術(shù)學建設(shè)成為一個系統(tǒng)性知識的人文學科。
基于上述范疇的基本理論研究,若與其他學科相交叉、相結(jié)合,又當形成相應的交叉學科和新理論、新方法。道一先生進一步提出有可能產(chǎn)生和出現(xiàn)的新學科如中國藝術(shù)思維學、藝術(shù)文化學、藝術(shù)社會學、藝術(shù)心理學、藝術(shù)倫理學、宗教藝術(shù)學、藝術(shù)考古學、藝術(shù)經(jīng)濟學、藝術(shù)市場學、工業(yè)藝術(shù)學、環(huán)境藝術(shù)學等等,指出:“隨著藝術(shù)學的深入研究和逐漸拓展,以及若干分支學科的建立,必將成為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一大門類,而藝術(shù)學的建立,又給藝術(shù)實踐本身以科學指導,促進藝術(shù)的繁榮”。這應是藝術(shù)學建立的價值所在。
兩年后,對藝術(shù)學的進一步的思考和對社會上的種種認識,道一先生又撰寫了《關(guān)于中國藝術(shù)學的建立問題》的長文,從正名開始,到提出“中國藝術(shù)學”的建構(gòu)、以及對西方相關(guān)理論的分析,都作了進一步的探討,使其建構(gòu)中國藝術(shù)學構(gòu)想的思想來源和背景更為清晰。我認為,先生從正名開始,對各種相關(guān)議論做的理論剖析和表述,不僅深入闡述了藝術(shù)學與美學、藝術(shù)學與美術(shù)學、中國藝術(shù)學與西方藝術(shù)學之間的諸多關(guān)系和理論,使藝術(shù)學和中國藝術(shù)學的建構(gòu)更為清晰和自覺;而且可以看到,中國藝術(shù)學理論體系的建構(gòu),正是建立在對東西方藝術(shù)歷史和現(xiàn)實的發(fā)展、對東西方藝術(shù)哲學、美學乃至藝術(shù)學的形成和發(fā)展的思考和把握基礎(chǔ)之上的產(chǎn)物。
道一先生關(guān)于藝術(shù)學的諸多理論與思考,無疑奠定了當代中國藝術(shù)學建構(gòu)的一個重要基礎(chǔ)。在他的操持下,當代中國第一個藝術(shù)學系得以在東南大學建立。當然,中國藝術(shù)學作為學科的建立,僅僅是起點,如道一先生所言:“這是一項巨大的文化工程,需要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共同努力。一個民族要能像巨人般地站起來,沒有深厚的文化基礎(chǔ)和理論思維是不行的。”他是這么想的也是這樣努力的。
張道一先生的個人文集8部,還有與廉曉春等人的合集以及未發(fā)表的論文,字數(shù)超過300余萬字。而各種專著字數(shù)更多。這些著述大都寫于改革開放以來的30余年間。
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無論是學界還是社會,有一種勤奮學習的風氣,道一先生也不例外。90年代這種風氣漸衰,物欲開始橫流,不少學人已無心于學問,至21世紀以來的10年,不少學人不僅無心于學問,更是以學問為工具,游走于官場與江湖之間,以致學術(shù)上的假冒偽劣盛行。在這樣的氛圍中,道一先生作為一介學者或文人,并未隨大流,更未曾想以學術(shù)作為謀權(quán)謀利之工具,而是以學術(shù)探討為日課,以學術(shù)真理的探索為目標,日日如此,他把握住了改革開放以來這難得的30余年寶貴時光,也把握住了自己,在從民藝學到藝術(shù)學的整個藝術(shù)研究的范圍中,默默前行,為中國藝術(shù)學研究奉獻出了其他人難以望其項背的巨大貢獻,他的各種著述,無疑都是一塊塊豐碑,雋刻著先生數(shù)十年的努力,也雋刻著真正中國知識分子的勤奮與真誠。